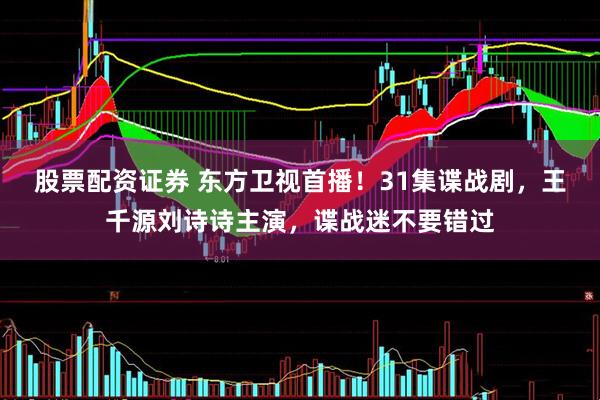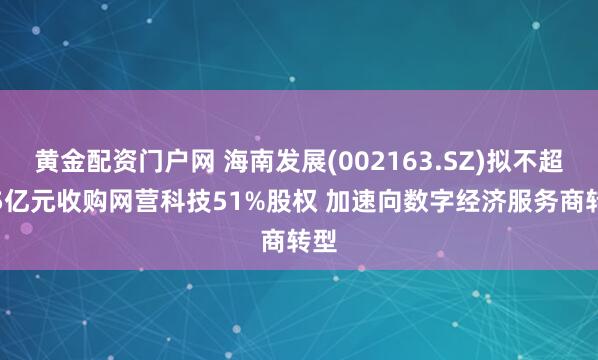7月7日,山东泰安肥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两份不起诉决定书,认定“山东入室抢婴案”中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刘某强夫妇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炒股股票配资网站,但因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决定对二人不起诉。
该不起诉决定一经媒体公开,毫无意外引来舆论关注和批评声浪。以自然理性观察,无论如何,一纸不起诉决定书,终结不了长达十八年的罪恶。该案件要回溯至2006年12月4日凌晨,曾某某等四人经预谋后,持械闯入肥城市王庄镇后于村姜某家中,暴力控制两位老人,将仅8个月大的男婴姜甲儒抢走。次日,曾某某等人以28600元将姜甲儒卖给刘某强夫妇。买家为其取名“刘恩正”,并在济宁市办理虚假户籍,彻底切断了孩子与原生家庭的联系。
2024年1月18日,刘某强夫妇被抓获,检方认定其收买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但笔锋一转,又以“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追诉时效仅5年”为由,认定刘某强夫妇从2006年犯罪至2024年归案,已远超时效期限,故不予起诉。被害人代理律师则当庭表示将申诉,其理由是买主明知儿童系被拐儿童且在收买后还通过假户口“逃避侦查”,应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追诉时效制度本为平衡社会关系稳定与司法正义而设。这一制度的逻辑基础在于:犯罪经过足够长时间,大多犯罪证据或已湮灭,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可能已消减。然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迥异于普通罪行,其罪恶绝不止于买卖行为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如绑架罪、非法拘禁罪等,追诉时效也不能从绑架那一刻起算,只要对被害人控制状态持续,就等同于侵害持续,犯罪行为尚未停止。
回到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其法理深意与自然理性并不冲突。当被拐儿童未能归家,身份认同权、家庭成长权便遭系统性剥夺,原生家庭的精神创伤随时间发酵成永不结痂的伤口。姜甲儒生母的控诉“不能放过他们”,字泣血。这种贯穿整个控制期的侵害,正是持续犯的法理本质——只要被害人仍被非法控制,法益侵害便处于持续状态。若仅因时间流逝便豁免刑责,无异于纵容“时间洗白罪恶”的荒诞逻辑。
而现行司法实践将收买行为机械归类为“行为犯”,实为对犯罪本质的误读。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而言,其犯罪形态绝非仅限于“买卖”行为发生的那一瞬间。从法益侵害看,收买行为不仅侵犯个体人身自由,更摧毁家庭伦理根基。刘某强夫妇为男婴办理虚假户籍,正是制造身份隔离以规避法律追溯的明证。这种系统性割裂血缘纽带的行为,使伤害伴随控制状态持续蔓延。更需警醒的是,拐卖链条中买方需求常直接诱发犯罪。本案中,正是刘某强夫妇“求购男孩”的意向,才促使了曾某某策划入室抢劫。司法若割裂处理拐卖者与收买者,忽视犯罪共生性,实则消解了“买卖同责”的立法精神。当人贩子面临审判而买主却能借时效脱罪,司法正义便沦为了残破的法网。
破解困局,亟需回归持续犯的法理正轨。呼吁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以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被拐妇女儿童尚未被解救,收买犯罪的追诉时效即处于中止状态。此举无需突破现行刑法框架,仅需对第八十九条“继续状态”条款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将收买行为与后续控制视为整体侵害过程。同时须激活刑法第八十八条“逃避侦查”条款的现实生命力——将办理假户口、洗白身份、阻碍寻亲等隐蔽手段纳入“逃避侦查”范畴,堵住买主借制度漏洞金蝉脱壳的暗道。更应深挖犯罪链条的共生本质,对“定制化收买”行为适用共犯理论数罪并罚,以严密的法网回应“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社会共识。
法律不能沦为时间的“人质”,更不应是罪恶的漂白剂。当被拐家庭手捧不起诉决定书质问正义何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均当回归常识:买卖行为的完成,绝不等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的终结,更不是被害人噩梦的终结。让追诉时效从解救之日而非伤害发生之日开始计时,才是对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的真正忠诚。
文/王顾左右炒股股票配资网站
辉煌优配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